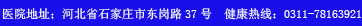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,被称为怪爷,晚年
2025/5/4 来源:不详他不抽烟不喝酒,一生就爱收古董。
他说:“予所收藏,不必终于身,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序。”
他叫张伯驹,在民国时期和爱新觉罗溥侗、张学良以及袁克文三人齐名,被称为京城四少。
虽然是官宦世家公子,但高起点的张伯驹并未选择军、政、商中的任意一条,而是顶着母亲口中的“不成器和败家子”,走出了一条“烧钱”的道路,他集收藏学家、书画学家、诗词学家以及戏剧研究家于一身,被称为民国的“文化奇人”。
今天我们来了解下张公子“挥霍千金只为画,千金散尽不复来”的跌宕人生。
少年张伯驹一、出生富贵未有惜,少年天性心中意
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,他的生父叫张锦芳,是个晚清廪生,在当地口碑较好,5岁时张伯驹被其过继给了子女早夭的哥哥张镇芳。
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,也是袁世凯嫂子的弟弟,也就是说张家和袁家有些亲戚关系,因张镇芳曾在经济上资助过袁世凯,年,当袁世凯升任临时大总统时,张镇芳也成为河南省的都督兼民政长,那年张伯驹14岁。
可以说张伯驹的少年时期正处于张家满门腾达的阶段,张镇芳很重视他的教育,少时即入私塾,待大些了又入读天津新学书院和政法学堂,和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是同学,妥妥的贵族教育。
待张伯驹17岁时,张镇芳为他安排了军界这条路,他被送进去了贵族子弟的“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”学习,20岁时张伯驹毕业(亦有说是肄业)。随后又被安排在吴佩孚、张作霖等人旗下担任参议,可以说他的起步颇高。
但张伯驹天性耿直,又书生意气,看着官场的尔虞我诈以及追名逐利,不由心生厌倦,萌生退意。虽然被给予厚望,但他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毅然决然的脱下戎装,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,回家继承家业。
这并不符合父母眼中的望子成龙,因此,他后来也说:“家里人并不喜欢我。”
但心性单一的少年并不在乎,他觉得做事要遵从自己的内心,在此后人生中他也一直遵循这个原则。
少年张伯驹二、机缘巧合遇丛碧,三十而立名雀起
年,27岁的张伯驹继承父业,担任盐业银行董事及总稽核,但他对此并不上心,每次去出差对账对他来说就是游玩。
年,29岁的张伯驹准备去银行对账,半途他突然兴起,转道去了琉璃厂,闲逛中他无意间看见了一副据说是康熙御笔“丛碧山房”的匾额,这个将《古文观止》倒背如流,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公子哥,只一眼就对这幅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他花了一千元,买下了这个匾额,回去后越看越爱,喜不自胜,无法自拔。他后来将自己的字改为“丛碧”,又将住所改称为“丛碧山房”,足以可见他对这幅字的喜爱。
此后张伯驹一发不可收拾,沉迷于书画,他像是开通任督二脉一般,找到了人生的乐趣。
也让本就有些书生意气的他,变得更加“清高”。
有人说张伯驹一不认官,二不认钱,独爱“诗词、书画和戏曲”,真是个怪人。从此也多了个“怪爷”的绰号。
三十而立,张伯驹毫无疑问是幸运的,他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意义。
青年张伯驹三、游春图里说气节,千金散尽求珍迹
年,已在收藏界颇有名气的张伯驹被人秘密告知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从溥仪手中流出,在琉璃厂云池山房经理马霁川手中,而他正在物色沪商想转手卖给洋人,以便获得高额利润。
张伯驹知道后怒不可支:一是,官宦家庭出生的他本就有强烈的名族气节;二是,沉迷书画后他对“古文物”更加了解,因此也更加珍惜。对于国宝流外之事,简直是痛心疾首。
他大骂:“马霁川要成为民族的败类吗?”
虽然心中气愤,但张伯驹还是急忙去找对方,得到肯定答复后,他要马霁川开价,是的,他想自己买回来。
哪知马霁川狮子大开口要求两黄金,要知道,民国的一两黄金(克)约现在的12万元人民币,也就是说这幅画总价约1亿元,而且那时一两黄金的消费能力不是现在所能比的。
彼时张家也渐败落,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但张伯驹刚花费了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《道服赞卷》,哪里还有空余的钱买这个,而且两明显有些虚高,但他又不敢直言反驳,只能先稳住对方。
回去后他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,终于让他想到一个办法,通过朋友,他联系上了时任故宫博物院的马衡院长,希望博物院可以买下,然而结果却让人遗憾,博物院经费不足无力收购。
但也带来一个好消息,马衡院长致函给了北平的古玩商会,告知不准此画出境,给了他稍许安稳。但张伯驹还是不放心,于是他亲自走遍琉璃厂的所有商铺,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叮嘱:“此画属于国宝,不可出境。”
一时间关于《游春图》的消息在文化界闹得满城风雨,马霁川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,他担心这画留在自己手上可能会不利,急于脱手,于是马上降价说只要两。
张伯驹听后欣喜若狂,心动不已,虽然这价格对于他来说还是无力支付,但他心里清楚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,未免节外生枝,他忍痛将自己最喜爱的一处豪宅出售,此宅占地15亩,原是清太监李莲英的私宅,也是张家最有价值的家产。
他以2.1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隔壁的辅仁大学,又将美元换成20条大黄鱼。可是临到交易之时,又突生变故,马霁川嫌弃黄金成色不好,要求再加20两。
于是张伯驹夫人潘素又变卖了部分首饰,才凑够数额,最终换得《游春图》。
张伯驹说,收藏有两大要件“才”和“财”。对于前者,在日积月累之下,张伯驹的鉴赏水平已在北京文化界颇有名气,已达到较高水准;但对于后者,张家已在崩溃的边缘。
然而张伯驹还是不为所动,只要是看中的,他有时在潘素面前打滚也要求来。
张伯驹和潘素四、飞来横祸身危殆,嗜画如命巧留遗
张伯驹对收藏精品珍惜的程度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。
年的一天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,张伯驹乘坐自己的小汽车出门去银行上班,哪知刚出巷口就被三人持枪拦住,那三人快速登跃上车,控制住了张伯驹后将司机踢了下来,扬长而去。
消息第二日传来,绑匪要求赎金个金条,否则撕票。
潘素焦急不已,家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钱,除非变卖字画。正在这时,张伯驹的拜把兄弟孙耀东也带来消息,张伯驹之所以被绑架是因为空降顶替了银行职工李某的位置,而李某的背后是汪伪76号特务所。
知道绑架者后让潘素稍微安定了下来,于是双方多番交涉,哪知绑匪传来消息说张伯驹已节食多日,现请潘素过去见一面。
两人见面后来不及诉说,潘素只听见张伯驹悄悄嘱咐她:“你怎么救我都不要紧,甚至你救不了我,都不要紧,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,你必须保护好,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潘素知道,张伯驹视那些字画如命,哪敢不听丈夫的话,且因朋友从中周旋,性命也能保全,于是双方几经谈判,终于在8个月后,以40根金条的价格将张伯驹赎回。
然而各大报刊却刊登了张伯驹“不愿卖画赎身,嗜画如命”的新闻,一时风头正盛,张伯驹未免树大招风,被迫举家搬迁离开上海。
年,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张伯驹夫妇将30年珍藏的8副精品字画无偿捐献给了国家,现均为故宫博物院的顶尖珍藏。
然而一年后他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,下派去了吉林。十年后又被勒令退职,下乡插队,因年迈被人嫌弃。
晚年的张伯驹生活清贫,但这个年轻时就潇洒不羁的公子哥,老了也是个豁达的老人,直至年正名,期间他从未有过怨言。
晚年潘素和张伯驹年,张伯驹因肺炎去世,享年84岁。
张伯驹一生共捐献了副字画(现价值上千亿),有挽联曰:“爱国家、爱民族,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,不惜身家性命;重道义、重友谊,冰雪肝胆赉志恋一统,豪气万古凌霄。”
有人说不知张伯驹则已,知道后再也不会忘记。这个民国的风流人物,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准则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,也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为什么。
生活可以没有荣华富贵,也可以承受流言蜚语,只要我知道自己心中的追求和意义,这才不枉此生。